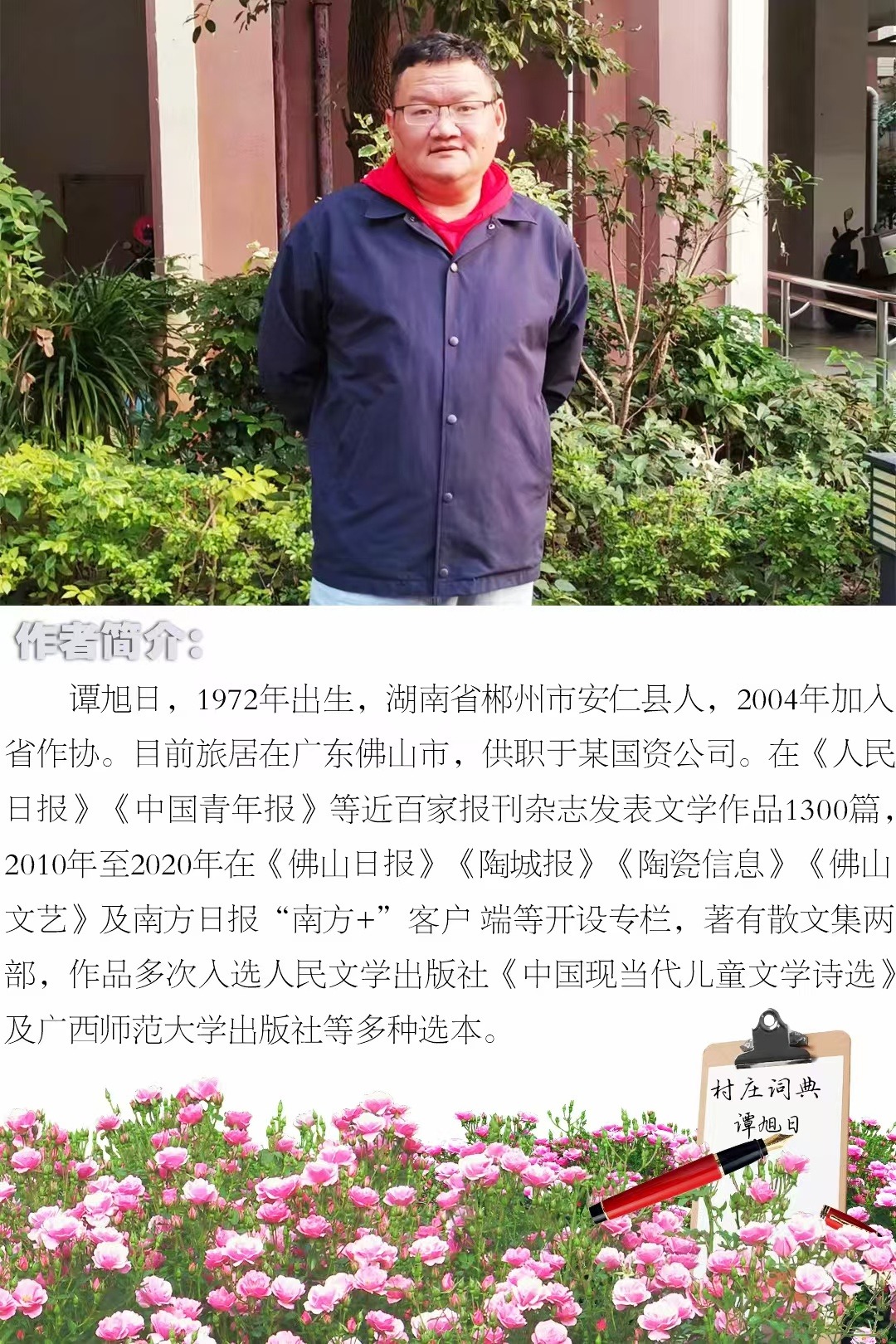前天晚上,黄泥铺的表哥在表亲群里发微信,告诉亲人们:当日下午六点十八分,八舅姥爷去世了。八舅姥爷是外婆最小的堂弟,九十高龄的人离世,算是福寿双全的人。在村子里,九十以上年龄离开叫喜丧。作为外婆的长孙辈,按照故乡的习俗,要在追悼会上办祭菜,又叫办汆。
在故乡,有句俗话:姑舅亲不亲,三代不隔心;姨表亲不亲,三代不见人。八舅姥爷的离去,这意味着在黄泥铺与我外婆近亲的人全部离去。那种往昔的亲情,在亲人离世的瞬间,便像烟云一样飘散开来。二哥看到消息后,及时打电话给长兄和我,商议着办一次祭菜。这在黄泥铺,是外亲与舅亲必要的一道礼行,算是一种祭奠与告别,也算是对至亲最后的一种敬畏。
二哥说,八舅姥爷的子嗣今儿个下午披麻戴孝到老家来告丧。外婆生前三个儿子未成年离世,母亲作为长女,承担了外婆的养老送终。按照故乡的礼法,我们自然作为外婆的孙辈代孝,自然要亲近许多。
小时候,我们常常随着外婆去她娘家走动。外婆经常带我们去她的兄弟姐妹家,一旦有喜事,也会去她的堂弟堂妹家走动一番。外婆去世前,我们与黄泥铺的亲人一直走得很近。八舅姥爷是外婆最小的堂弟,比我母亲也只大了八九岁。我们每次去黄泥铺,在白沙矿务局跑煤炭生意的八舅姥爷特别讨人喜欢。但凡有空,他就会带我们到东湖圩上赶集,买油糍粑,买甘蔗,买荸荠,或到供销社买水果纸包糖,买桔子罐头,买麦乳精。八舅姥爷算是黄泥铺村上敢想敢闯的青年,有点闲钱,也是青年中的佼佼者。
八舅姥爷少年时倜傥不羁,三十多岁后才肯娶亲。娶了婆娘后,他带我们去东湖圩上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,但他家里却总有意想不到的食物,比如说,上海的大白兔奶糖,衡阳的麻饼,耒阳市食品厂的油枣、杨梅酥、寸丝根、烤蛋糕片、猪耳朵片。每次去他家,我们都惊喜而又激动。因为,在改革开放前,这些食物少之又少,一般人家也是消费不起的。八舅姥爷家里的食物,也让我特别迷恋去他家做客。外婆也懒得管我,八舅姥爷的婆娘也是个明事理的人,对我也特别关爱。正是这种亲情,让我们与黄泥铺的联系一直延续至今。
今夜,二哥再一次打来电话,说礼师已经选好八舅姥爷登山的日期,合了八字后,农历二十三开追悼会,开的是日舞堂,不是夜舞堂,前者是有成就的家庭要整天举办追悼会,后者仅夜间举办,次日登山。
八舅姥爷的三崽一女也是蛮有名堂,日子过得可以。老大在广州铁路局工作,老二在省城长沙从政,老三在耒阳市某中学当副校长,小女则在军队院校从教,是一名教授。这样的家庭,自然将喜丧办得隆重些。
二哥在微信里列了一个菜单,要一一置办。在黄泥铺,一般亲人办祭菜,为七样。兄弟姊妹间,要十碗荤。鸡鸭鱼肉,经典四样,配上猪头、猪肚、猪脚、猪耳,还得配上粉丝、墨鱼。水果三样,俗称三鲜。鸡蛋十个,寓意喜丧完美。置办好了后,要到屋后的屋背山上摘来侧柏叶,在每件荤菜上插上柏树枝,寓意庄重哀悼。然后摆上长方盛器——桥杠(又叫抬伙)。
二哥说,为了表示心意,旗、锣、凉伞从村里祠堂借;乐声队要叫上两列,一支锣鼓喇叭,一支洋鼓洋号;备好花圈,炮竹,烛火,还有丧事专用的、插引线硝的铁制炮,还有烟花,再到村子里叫上几个老者。一场浩大的仪式,从我们故乡出发,到达黄泥铺。二哥在村里做书记,平常又热心帮助乡亲,叫七八个帮手的,不难,很快就凑齐了班子。今夜,乐声班子的锣鼓喇叭,开始操练起来。因为不论在老家,还是黄泥铺,我们虽然不同地区,但民俗却是相通的。敲锣打鼓,撑旗打伞,放炮点灯,浩浩荡荡把这一抬祭菜送过去,是一个家族的礼节,也是对一个亡者最后的敬仰。
我忽然想起,事死如事生,仿佛就是在备一桌走亲访友时的饭食,那种以饮食告别的方式,亦是故乡人对亲人最后的告慰。故乡人讲究礼数,讲究吉数。唯一不同的是,当线香点燃,当哀乐和鞭炮声响起,在钱纸点燃的过程中,那种气息是沉重的,揪心的。
我会想起,当追悼会的乐器一响,礼师一开腔,哀乐声穿过黄泥铺早春的薄雾,在屋后的山坳里回荡。线香燃到一半时,起了风,连蜡烛都呜呜作响,杠桥上的供品被风吹得微微晃动,仿佛八舅姥爷回来了,在“享用”祭菜。唯有那摇曳的烛火,让我恍惚间仿佛看见他站在黄泥铺对面的山岗上,还是少年时清纯的模样。
这一桌祭菜,不仅送走了八舅姥爷,也送走了一个至亲时代。那些关于爱,关于少年,关于外婆,在催泪的唢呐声中,一点点远去,一点点撕裂,直到飞散得无影无踪,又无边无际。